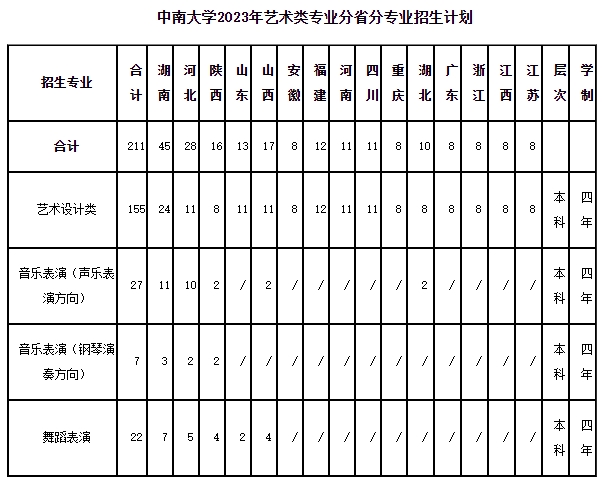中国画的意义世界
一
钱钟书曾经指出,“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评画时赏识王世祯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评诗时却赏识‘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 究竟什么是“实”什么是“虚”?为什么画以“虚”胜而诗却以“实”胜?对于这些问题,钱钟书没有深究,也许在他眼里,这是中国传统文艺批评中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但正是在这些表面上明白不过的道理中,却潜伏着矛盾和困惑,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画都比诗“实”,诗都比画“虚”。诗言志,画图形; “形”在外是“实”,“志”在内是“虚”。因此,黑格尔说诗歌比绘画更高级,更具有精神性,也更“虚”。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来解释这里的矛盾:本身是“虚”的诗相反要追求“实”的境界,本身是“实”的画相反要追求“虚”的境界。但这种辩证法式的解释,难免给人一种简单草率之嫌。
徐复观的一段文字似乎可以看作这里的“虚”与“实”的注释。他说:“我国文学源于五经。这是与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结合的带有实用性很强的大传统。因此,庄学思想,在文学上虽曾落实于山水田园之上,但依然只能成为文学的一支流;而文学中的山水田园,依然会带有浓厚地人文气息。这对庄学而言,还超越得不纯不净。庄学的纯净之姿,只能在以山水为主的自然画中呈现。” 按照徐复观的解释,诗文之所以是“实”,因为它跟政治、社会、人生密切相关,与实用性密切相关;绘画之所以是“虚”,因为它超越了各种人事的实用性的考虑,只是以纯净的自然山水为对象。套用西方美学的术语,诗文之所以是“实”,因为它是“有利害”考虑的,我们与事物之间的“心理距离”(psychical distance)太近;绘画之所以是“虚”,因为它超越了利害考虑,是无利害的(disinterested),我们与事物之间保持着适当的“心理距离”。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诗歌更容易接近利害考虑而绘画却更容易超越利害考虑?徐复观对此没有进一步的说明。我想除了受到传统的影响之外,就像徐复观所主张的那样,中国诗文之所以不能完全落实艺术精神是因其源于五经,受到注重实用性的儒家传统的影响,媒介的不同也是一个主要原因。中国诗文不仅源于五经,而且在其发展演变中还很难摆脱五经的影响,这是由诗文使用的语言媒介的本质特征决定的。语言,不管多么诗化的语言,总有概念化的倾向,从而为阐释者作道德文章的引申提供了可能。而绘画,特别是文人山水画,由于其运用的材料主要是笔墨,是一些不能被概念化的东西,所以比起诗文来,更容易超越儒家政治伦理思想的局限,而接近由庄学发展起来的自然的艺术精神。
诗文与绘画之间的媒介不同,不仅可以用来进一步说明为什么中国诗文尚“实”,而中国绘画崇“虚”,而且可以以此为契机来阐释中国画的意义世界。
二
如果中国诗文因为摆脱不了概念理解因而显得很“实”的话,那么中国绘画的“虚”就体现在它呈现了我们在概念之前或之下对事物的理解。如果我们将经由概念的理解称之为理解(understanding)或概念理解的话,那么在概念之前或之下的理解就是前理解(pre-understanding)或前概念理解;如果我们在理解中获得的是关于事物的知识(knowledge)的话,那么在前理解中获得的是关于事物的前知识(foreknowledge);如果我们将在概念理解的知识中显现的世界称之为真实(real)世界的话,那么在前概念理解的前知识中显现的世界就是前真实(pre-real)世界。前真实世界是一个比真实世界更本真、更源初的世界。
那么,究竟什么是前理解?什么是事物的前知识?什么是前真实世界?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跟与此相应的理解、知识和真实等对照起来说明。概念是一类事物所共有的本质特征,比如不管现实世界中的桌子多么千差万别,桌子的概念始终保持同一。概念理解,就是将不同的桌子纳入同一个桌子概念之下的理解,从而获得关于桌子的稳定的、普遍有效的知识。根据认识论的一般看法,只有掌握了桌子的概念和知识,我们才把握了桌子的本质,洞察了桌子的真相。但桌子的概念并不是桌子。没有一张桌子能够完全符合桌子的概念,就像没有任何一个实际的正方形像正方形的概念所要求的那样方。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通过概念来理解周围事物,周围事物总是显现为相对稳定和普遍有效的知识。但事物在概念理解中显现的稳定的知识样态,并不是事物的本真样态,并不是事物本身。也就是说,我们平时信以为真的事物其实并不真实。我们的概念理解至少从两个方面对事物进行了歪曲。首先是回忆再现的歪曲,其次是概念再现的歪曲。我们对事物的概念理解总是对已经在感知中出现过的事物的理解,如果说在感知中出现的事物是事物第一次与我们照面的话,那么在概念理解中出现的事物就是事物第二次与我们照面,是对第一次与我们照面的那个事物的回忆。这就是感知只能感知在场的事物而概念理解却可以理解不在场的事物的原因。但借助回忆显现的事物总不是事物本身,至少它削弱了来自事物的存在意义上的冲击力,我们感受不到事物的压力,或者说,事物不再是野性的事物,不再是体现必然性的事物,它已经被改造或驯化得服从我们的想像以便我们可以用概念来把握它了。这是概念理解对事物的第一次歪曲。第二次歪曲是让事物在概念中出现。概念理解总是借助概念进行的,任何概念都只能描述事物的一般特征,在概念理解中出现的事物也总是显现出符合一般特征的特征,它自身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被剪裁掉了。从这种意义上说,概念理解是对事物的强暴。
中国画家并不描绘那个在概念理解中再现的貌似真实而其实不真的真实世界,相反他们要捕捉那个在前概念理解中呈现的貌似不真而其实本真的前真实世界。中国画的意义世界就是在概念理解之前或之下的那个貌似不真而其实本真的前真实世界。
三
现在的问题是:所谓概念之前或之下的前理解就是一种怎样的理解?存在这样一种能够通达事物本真存在或事物本身的理解吗?从中国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前理解是肯定存在的,借用庄子庖丁解牛的寓言中的表达方式,前理解是“神遇”而不是“目视”,或者更一般地说是“以道观之”。究竟什么是“神遇”或“以道观之”?清代画家邹一桂《小山画谱》中有段记载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个问题:
宋曾云巢无疑,工画草虫,年愈迈愈精。或问其何传,无疑笑曰:“此岂有法可传哉?某自少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丛间观之,于是斯得其天。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也?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
我们从这个故事中可以区分两种理解草虫的方式:一种是对着草虫时对草虫的理解,一种是与草虫融为一体时对草虫的理解。我们对着草虫时对草虫的理解总不能摆脱草虫概念的幕帐,总是用对草虫的一般的稳定的知识来掩盖草虫本身。与草虫融为一体时对草虫的理解没有草虫概念的中介,或者说突破了草虫概念的硬壳,这就是所谓的概念之前或之下的前理解,在这种前理解中,草虫能够显现它的本真样态(即所谓“斯得其天”)。
当代许多西方哲学家都否定有这种能够显现事物本身的前理解。比如,根据尼采的透视主义(perspectivism),根本不可能存在事物本身,所有的事物都是在语言解释中构成的,不存在独立于解释之外的事物。这种主张也被称之为普遍的解释学立场。如果连事物本身都不存在,哪来的对事物本身的洞见?当代分析哲学家将那种事物可以离开解释而存在的主张,称之为“被给予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given)。分析哲学要破除的就是这种神话。不过,另一些哲学家主张,即使不存在离开解释而存在的事物,但至少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解释,在其中的一种解释中我们可以更接近事物本身。比如,梅洛-庞蒂(Merleau-Ponty)的现象学考虑的核心问题就是那种在概念理解之下的身体感知的问题。我们的身体感官(bodily sense-organs)具有一种在思想、意识、心灵之下的感知能力,总之,具有一种在人之下(sub-personal perceptions)的感知能力。这种感知在我们在世界中存在时就已经发生了。我们关于世界的概念理解,事实上只不过是对这种已经发生的身体感知的回忆而已。再如,以发现默识知识或默识认识闻名于世的博兰尼(Michael Polanyi)也表达了与梅洛-庞蒂类似的思想。在博兰尼看来,我们对事物的意识可以区分为集中意识(focal awareness)和辅助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由心灵发出的集中意识是“对”(to)对象的意识,由身体发出的辅助意识是“从”(from)对象和身体自身的意识。因为在后一种情况下,对象已经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从对象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从身体的意识,也可以称之为“寓居”(indwelling)或“内化”(interiorization)的意识。这种辅助意识所得到是事物的存在性意义(existential meaning),是非名言知识(inarticulate knowledge);与之相对,集中意识所得到的是指示性或表象性意义(denotative, representative meaning),是名言知识(articulate knowledge)。所谓名言知识就是概念理解所获得的知识,所谓非名言知识就是前概念理解所获得的意义或意蕴。
无论是梅洛-庞蒂的身体感知还是博兰尼的默识认识,它们都指一种在概念理解之下或之前的理解。如果说概念理解主要是由我们的意识作出的,那么前概念理解主要是由我们的身体作出的。由此,我们可以总起来说,所谓前概念理解,就是我们与事物融为一体时对事物的内在领会。
此外,还需要指出的是,从邹一桂所讲的那个故事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所谓前概念理解并不是指人在没有掌握概念之前的理解,而是指有了概念理解的人在超越或还原概念理解之后的理解。这一点可以很好地反驳分析哲学的“被给予神话”的指控,同时也可以很好地避免将前概念理解等同为概念理解尚未发育完善的原始人或婴儿的理解这种普遍的误解。
四
如果说在概念理解中显现的事物是稳定的“实在”,那么在前概念理解中的事物又是什么样子呢?由于前概念理解很容易为概念理解所遮蔽,人们就将透过概念理解显现的稳定的事物“实在”当作事物本身,但我们已经指明它不是事物本身,而是对事物的双重歪曲。什么是事物没有经过概念理解歪曲的样子?这是一个非常有欺骗性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容易陷入对事物的概念描述之中。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在概念理解歪曲之前的事物是“虚”的。这里的“虚”并不是它不存在,也不是说它虚幻不真。那么“虚”究竟指的是什么?
“虚”首先是虚掉事物稳定的实在性,一旦消解了事物稳定的实在性之后,我们就不会固执地以为事物是一成不变的,或者只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是真的事物。在前概念理解中显现的事物由于与理解者的存在紧密相关,而理解者的存在又是有时间性的,或者说是在时间中展开的,在时间中展开的存在是有变化的,因此在前理解中显现的事物总是活泼泼的、幻化生成的,但这并不等于它们是虚幻不真的。这种变化而真实的东西是如何可能呢?因为我们一般将真理解为确定不移的,没有稳定性的事物我们根本就无法辨认它的身份,从而无法断定我们关于它的认识的真假。不过,我们可以设想事物在时间之流中是变动不居的,而事物在时间之流中的每个时间点上是确定不移的,这样我们至少可以说事物在每个时间点上都是千真万确的,它们之间的真实性是不可比较、不可分级的。这就是我所说的“刹那真”的观念。概念理解追求的是事物在时间流中的恒定性,前概念理解追求的是事物在时间点上的恒定性。在概念理解中的同一个事物,在前概念理解中可以千姿百态。事物的这些千姿百态都是同样地真实,甚至可以更极端地将同一个事物的千姿百态看作千姿百态的不同事物。我们可以进一步将概念理解意义上的真称之为“衍生真”,将前概念理解意义上的真称之为“原生真”。“衍生真”之间的真实性是可以比较、可以分级的,“原生真”之间的真实性是不可比较、不可分级的。比如,今天对月亮的科学认识(概念理解中的“衍生真”)显然比先秦时期更准确,但不能因此说今天人们对月亮的感受(前概念理解中的“原生真”)比先秦时期更真实。我们不仅不可以比较今人和古人在前理解中所把握的事物的真实程度,也不可以比较同一时代的自我与他人在前理解中所把握的事物的真实程度,甚至不可比较同一个自我在不同时间点上在前理解中所把握的事物的真实程度。在我的前理解中刹那现起的月亮可以不同于在你的前理解中刹那现起的月亮,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我当中只有一人的前理解是真实的;在我此时的前理解中刹那现起的月亮可以不同于在我彼时的前理解中刹那现起的月亮,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于彼此不同时间点中的前理解只有一种是真实的。总之,事物的原生真实样态可以是多种多样,我把这种主张称之为存有性多元论或在场性多元论(pluralism of presence)。
但我们并没有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相反,这里有一种绝对性,一种必然性,一种对必然的真实感受的绝对服从。只要我们设身处地地感受,只要我们像人一样地去感受,就能够感受到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原初真实,感觉到它们都是同样地真的。这种同样的真的感受,不是来源于这些原初的真都是一样,而是因为它们都是同样的不一样;它们都触及到了自己的存在的根底,但在各自的根底上却表现得千差万别。相反,人们在概念理解层次上的认识尽管被证明是绝对真实的,但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被牛顿证明是错误的,牛顿的物理学被爱因斯坦证明是错误的,爱因斯坦的物理学也一定会被后来者证明是错误的。但没有人去证明荷马是错误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没有人去读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却有人去读荷马史诗的原因。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造成事物在前理解中显现的前真实样态的差异性,事实上是理解者的风格的显现。所谓风格,按照杜夫海纳的理解,在根本上是一种情感特质。每个人给人不同的风格感觉或印象,源于每个人的不同的情感特质。这种不同的情感特质会给前理解中显现的事物定下不同的情感基调,从而使事物体现出不同的风格。就艺术欣赏而言,任何艺术作品都有它的情感基调或风格,必须把握作品的情感基调或风格才能准确地理解艺术作品。作品的情感基调与作者的情感气质类似,因此我们可以用“欢快”来说莫扎特的音乐和莫扎特本人。这就表明,在莫扎特和莫扎特的音乐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不仅是情感性的,而且是先验的。“欢快”这个先验的情感范畴决定了莫扎特成为莫扎特,决定了莫扎特的音乐成为莫扎特的音乐。同时,我们只有通过“欢快”这个情感范畴才能进入莫扎特及其音乐的审美世界。
由于在前理解中显现的世界是艺术家或感知者的情感特质或风格的显现,因此可以说在前理解中显现的世界是具有个人色彩的世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主观的世界。但是,这里的主观不能理解为主观偏见,而应该理解为有差异的个体的真实存在样态。我将这种主观理解为一种“无主观性的主观心灵”。总是,中国画表现的那个前真实世界,是一个比主观主观、比客观更客观的世界,是那个在主客体尚未分裂之前的原初世界。
五
让我提出一个大胆的主张:中国画对前真实世界的揭示,可以让业已终结的艺术重获新生。为了阐明这个主张,让我简单介绍所谓的艺术终结论的主张。
“艺术终结”(end of art)是黑格尔(G. W. F. Hegel)在他的美学讲演中提出的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观点。在黑格尔看来,随着理念的发展,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深邃,以至于完全超出了感性材料或手段的表现范围,这时我们就只能通过哲学的理性思考才能把握理念,而不能以艺术的感性形式来表现理念,艺术因此为哲学所取代。受黑格尔艺术终结论的启发,丹托(A. Danto)阐发了一种更为精致的艺术终结论。在丹托看来,艺术发展的历史就是艺术不断通过自我认识达到自我实现的历史,换句话说,是艺术不断认识自己本质的历史,艺术发展史的最终目的,就是艺术最终认识到自己是“艺术界”(artworld)的产物,是理论解释的结果,是一种被理论氛围(an atmosphere of theory)所环绕的存在。艺术发展的最终目的在20世纪的艺术实践中已经达到。一旦认识到自己的本性,艺术发展的历史就走到了尽头,因为作为理论解释的艺术其实就是哲学,艺术最终在哲学中终结了自己的发展。今天的艺术处于它的“后历史”(post-historical)阶段,由于艺术的所有可能性已经被实践过了,因此今天的艺术实践只是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各种艺术形式的重复,它已经不可能再给人以惊奇的效果。
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主张艺术总是不断创新的。任何非创新的艺术实践都只是一种习惯,而不是真正的艺术实践。20世纪的艺术实践,穷尽了艺术所有的可能性,因此艺术不可能再向前发展了,艺术的历史也就终结了。
摆脱艺术终结的最好方式,就是为艺术寻找一个这样的领域,它能永远满足艺术家创新的冲动且在根本上抵制理论的解释。这个领域就是中国画所追求的意义世界,一个在概念理解之下或之前的前真实世界。前真实世界是常新的、不可重复的,而且是不能用概念来解释的。在前真实世界中工作的艺术家不会有影响的焦虑,因为他的工作是唯一的、不可重复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艺术终结之后的艺术,是表现前真实世界的艺术。这并不是说艺术将在形式上向中国画回归,而是在精神上去追求中国画的理想。
我还要更冒险地主张,这种新的艺术方向,不仅对于艺术的自我拯救非常重要,而且有助于人类摆脱生存困境。如果一切都可以用概念来表达,那么就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如果果真这样的话,人类最终就会变成信息终端。让我以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所讲的一个科幻故事来说明这个观点。
想像两个表面上完全相同的观众,他们能够对面前的艺术作品做出完全相同的解释。其中一个是人类,他为他所看到和解释的东西而兴奋不已。而另一个只是一个经验不到任何可感知性质的电子人,它感觉不到快乐,实际上根本感觉不到任何情感,它只是为了做解释陈述而机械地处理感知的和艺术界的数据。由于这个原因,即便电子人的解释陈述在描述上比人类的解释陈述要更加精确,我们仍然可以说人类对艺术的一般反应要更为优越,而由于电子人完全没有感受到任何东西,因此它根本就没有理解艺术到底是什么。现在进一步想像要是彻底将审美经验从我们人类文明中剔除出去,那么我们就会完全被改造为那种电子人或者被电子人所灭绝。
舒斯特曼这里所讲的那种审美经验,就是我所说的那种前概念理解,只有突破概念的幕帐我们才能获得关于事物的在场经验,而在场经验又是人生的真正组成部分。在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的今天,能够保持和表现在场经验的艺术显得尤其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人类的未来:人究竟是进化为信息终端,还是继续保持血肉之躯?
《清华美术》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