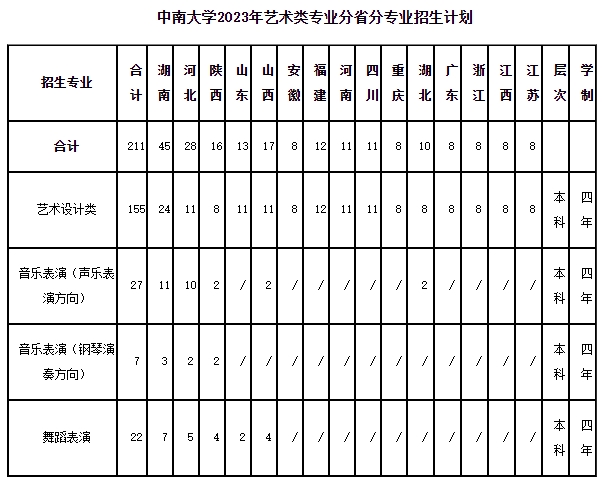1945年以来的西方雕塑(七)
动态艺术
在战后的艺术运动中,没有哪一种形式像动态艺术这样远离大众的趣味,从某种程度上讲,动态艺术仅仅是一种口味变换的产物。在工艺技术充斥的60年代,人们狂热地崇尚:工艺本身以及那些设计新颖奇巧的消费品。到了70年代,人们的这种狂热被厌倦和反思所取代,随之形成了一种对工艺技术和消费者至上主义充满敌意的气氛。此外,动态艺术也是其自身意外成功的受害者。随着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蓬勃兴起,动态艺术被作为这类机构招引公众的一种理想的招牌。动态艺术被认为是属于一种直接娱乐形式的前卫艺术。一些规模盛大的展览--最为雄心勃勃的要算1967年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光线与运动》展览--的确吸引了数量可观的观众,但这些参观者大都失望而归。他们已经充分领略了外面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博物馆内的技术就显得乏味和幼稚了,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但却被大家所忽视,这就是当代艺术的世界地理格局。纽约的优势地位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这成为欧洲评论家们的一块心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动态艺术是被人为地扶持起来对付这种局面,以期推动欧洲艺术的复兴。但归根结蒂,动态艺术总是不如美国所进行的艺术运动那么激进,因而轻而易举地被极少艺术扫入旁门。
动态艺术的家谱混杂,而且动态艺术作品往往在创作意图上大相径庭,以至把它们统统归于同一类别之中多少违背了它们的初衷。但总的来讲,动态艺术属于构成主义的一个晚期分支。实际上,一些早期的构成派艺术家就已经实验过包含运动的艺术作品,其中之一是亚历山大·洛德申柯,他有一件作品是一个悬垂装置,上面包括一系列嵌套旋转的开口圆环。另外一位是诺姆加波,他1920年创作的震动细杆被普遍认为是其后所有带有动力装置艺术作品的鼻祖。由于构成主义的影响如此之大,致使一些作品中没有真正和明显运动的艺术家们也被划入动态艺术之列。典型的例子就是巴西的雕塑家西尔吉奥·德·卡玛戈的一些作品明显地表明他与乌拉圭画家乔甘·扎利斯-加利亚的联系,后者是1930年巴黎的《圆与方》画派的创始人之一,后来构成主义思想在整个拉丁美洲的传播也应主要归功于他。卡玛戈主要在木头上创作浮雕。他在木头表面密密麻麻地刻上斜切而成的小圆柱体,或者以大量倾斜的方形平面充满表面。其结果是,该表面的整体性被打破,而且对光线的变换极为敏感。卡玛戈本人将自己的作品视为主要是一种沉思,就是当我们注视自然时所感觉到的那种思想的解放。他说道:"也许我的作品所产生的效果就是将任何靠近它的人的某些情绪解放、释放出来,这些情绪有点像当我们面对某些空间和景致,或当我们体味空间、声音和思想时所经常体验到的感觉。"对卡玛戈来说他那拥挤的表面试图造成一种无焦点的效果,而路易斯,奈维森作品所具有的同样效果几乎也毫不逊色,很难将他视为真正的动态艺术家,甚至在强调造成运动的幻觉而不是运动本身的艺术风格派别中也又难找到他的位置。
冈瑟·尤克是德国零派的成员之一(该派由他本人、海因茨·马克和奥托。彼埃尼组成,他们于1958年在杜塞尔多夫的彼埃尼工作室中举办了第一次共同展览)。冈瑟·尤克也使用被隔裂的表面来使艺术作品非物质化,强调作品所释放的视觉能量而不是其自身物质的重量和存在。尤克所采用的手段非常简单。他在作品表面钉上紧密排列在一起的钉子,这些钉子使光线衍射从而形成干扰波纹图案。这些钉子是墙上的浮雕,但尤也将它们用在三维物体上,比如像独立的立方体。这些浮雕有时又采用旋转圆盘的形式,其物理的运动增强了光衍射的效果。
卡玛戈的拉丁美洲同胞、委内瑞拉的耶苏-拉菲尔·索托将作品置于光学效果更加强烈的地方。他最典型的作品都包含有金属的细杆和圆盘,悬挂在一排细线前面一点的位置。物体在光学效果上被它们的背景所吞蚀了--我们愈试图盯住它们,它们看上去就愈非物质化,但这些作品几乎不是三维的,只有在它们的正前方的一个固定视角才能最好地观看。索托从物理上构造出了"浅空间"的区域,这最早出现在立体主义绘画中,并且可以在许多画家的作品中见到)、这些人之中包括像布里吉特·赖利和杰克逊·波洛克这样截然不同的画家。
在阿根廷艺术家朱里奥·勒·帕克的动态装置中,存在着名副其实的三维性。像在《连续的活动,连续的光》中一样,他的作品常常包含有悬挂在细线上的小反射镜,它们将光线折射向四面八方--这种光的效果,而不是产生这种效果的机械装置,构成了作品本身。但是人们不难发现这种小技巧几乎就和舞厅里那种轻快旋转的多棱镜面彩球一样。
希腊艺术家塔基斯追寻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他是一位更为重要而有趣的人物。他将运动中的艺术作品的概念与受禅宗影响的最简式的抽象主义结合在一起。后者在伊夫·克莱因的作品中也可见到。塔基斯的雕塑常常展示不可见的力,例如磁力。一股磁流可以吸引钢针克服重力作用而在空中悬浮;而电磁的通与断可以使充满正电荷和负电荷的钟摆随机舞蹈。塔基斯的作品吸引了60年代一些重要的前卫作家,其中包括威廉姆·布拉夫斯、格里高利·康索和阿伦·甘兹伯格,而他们又赋予他的作品半神秘的意义。布拉夫斯写到:"当你观察这些不安的、自由浮动的东西在不可见的山门中运动和咔嗒作响时,你可以听见金属在思想。"马塞尔·杜桑,达达派的创始人之一,也同意他的看法。他在一段有代表性的文字中称塔基斯为"磁性田野中的耕耘者。"但他所面临的困难过去是、现在还是,其作品基本土是相当简单的机械--它们太简单了,难以满足以它们为宇宙模型的设想。这些作品准确他说应该算是在展示自然中某些人们已熟知的物理力,更适于用来在中学的科学课上活跃气氛。
杜桑本人也时常从事动态作品的创作,而达达和超现实主义也是动态艺术的缘亲之一,对于法国人波尔·伯里的作品来说,它们所使用的那些几何形式更接近于超现实主义而不是构成主义。这些物体的特点在于其运动的隐秘性,像是试图逃脱观者的眼睛--将观者带入一个无生命物体的世界,那个世界隐藏着仇恨,并且从事着某种敌视人类的阴谋活动。
一些动态艺术家实际上将他们的雕塑从本质上看作是机械的演员,设计出来扮演一类特殊的角色,其表演的过程比其自身作为艺术作品的物质基础更为重要。在这条道路上进行雕塑创作的最早的人中有尼古拉·舍弗尔,他1912年生在匈牙利,并于1937年移居巴黎。在巴黎他以诺姆·加波和摩霍利-纳基所创立的构成主义风格开始创作并早在1948年就转向制作他称之为"空间运动"的雕塑。这是些可以反射光线的露天竖塔。50年代舍弗尔给这些建筑物增加进运动和声响;1956年,他与菲利浦电器公司合体创作出一件可对光和声做出反映的雕塑。他最为壮观的成就、也是整个动态艺术运动的巅峰之作是他于1961年在列日(比利时城市)建造的52米高的塔--其中运用了光、运动和音响效果。舍弗尔的雄心不仅限于此。他也构想在将来建造一座悬于吊架上的空中城市,用技术手段控制人类生存的环境。这些计划并没有付之实施,但舍弗尔在1968年的威尼斯双年展上荣获雕塑大奖,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
在少有的几位对70年代和80年代产生影响的动态艺术家中,有一位生于美国、定居英国的莉莲娜·利耶。早在1967年巴黎举办的"光线与运动"展览上她就已经被公认为是动态艺术运动中的重要人物,从那以后她完成了若干个修建喷泉和其它公共场所雕塑的政府定件。其中一项近期的工程(1983年完成)是《野物女士》,这是一个比真人大的带翅膀的女性人体,可以通过光信号对人类声音做出反应。利耶把它当作象征着下意识的思想通过机器在说话。她还为《野物女士》设计了一个名为《战争妇女》的陪伴,完成后这两个雕塑就可以对话了。
也许仍在活动的动态艺术运动的参加者最重要的是让·坦盖利。他与其他动态艺术家们不是出自一个体系。其他人的作品都源自构成主义,而从坦盖利的早期作品,像《三角架上的元机械》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达达运动的继承人。他那些摇摇欲坠的机器有时产生一种抑郁的效果,但更多的时候显得特别的欢乐和无政府主义。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包括《向纽约致敬》,是1960年为现代艺术博物馆创作的,这件作品通过其自我毁灭的设计说明了它的意义。坦盖利对他自己创作过程的描述表明,他的工作程序远远谈不上科学:
这是个人的事。我需要能够犹豫一会儿,产生怀疑,试试这个,试试那个做出点东西但又不知它是否有用……我不可能和其他人在一起工作……我独自处于我自己的混乱中会更舒服。我不能和其他任何一人一起陷入混乱,或其他两个人……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工作时我就陷入这种混乱之中,因为我有许多想法,有时候同时有三个主意,这时我一点也不知道该拿它们怎么办。
当大部分的动态艺术表现着对科学和技术的天真崇拜时,而坦盖利则对机器本质所具有的不完善和易犯错误表现出快乐的嘲弄,而另一方面也表现出某种同情:
也许我一点儿也不痛苦……但作品却是痛苦的……。其结果是充满了焦虑,但我并不焦虑。我试图将我在这世界上所见到的疯狂提炼出来,这种疯狂是我们工业的混乱状态所产生的对机器的疯狂;我将它表现出来,通过这种相当不可救药的机器,一种错乱的、疯狂的机器,站在那儿,站在它的平台上……一种西绪福斯(Sisiphus)机器,被阻塞着,毫无用处……当然我试图表达这种无望的、绝望的性质,但所表现的绝望更像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像一种颜色,就好像我是一个画家,画出一个可爱的蓝色天空。
坦盖利不仅与达达有关,还与保罗·克利(曾设计出一种吱吱叫的机器)的艺术有关。他也与考尔德有类同之处。考尔德常常被称为动态艺术的鼻祖之一,但他本人却更愿意避而远之。坦盖利与克利和考尔德这两位艺术家一样都具有一种幽默感,同时还具有对复杂事物的感知力,坦盖利的机器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它们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看上去表现出这位艺术家对其作品的责任感。而我们在下一章中所要谈到的极少艺术,则完全是另一种姿态了。
极少艺术
极少艺术给战后艺术世界带来了一次重要革命,它向艺术作品本身与观众个人和整个社会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深刻的质疑,极少艺术是现代派的和谐之中的一道裂口,一道至今没有愈合的裂口。波普艺术和超级现实主义艺术都可以认为包含了极少主义的因素,因为这两个流派的艺术家们都拒绝使用这个他们置身其中的社会所提供给他们的形象。但是他们至少还承认这个社会的存在。而极少艺术坚决否认作品本身之外任何引申的意义,以至于它们以牺牲绘画为代价极大地扩展雕塑的领域,因为绘画,即使是最抽象的部分,也仍然不可避免地具有引申的因素,任何平面上的设计都存在被视为某种暗喻或标志的危险。
最早一批的极少主义艺术家都希望创作出的作品,不带生气,不附情感,在感情和理智上都是封闭的。尽管许多极少主义的早期支持者都反对这一点(多少使艺术家们感到愤怒),并找出一大堆说辞证明极少主义艺术家首先采用的这种简单的几何形式产生了一种"良好的格式塔效果",也就是给观众造成了一种很舒服的心理环境。
极少主义这种艺术风格极其简化,但它不是无中生有的。它一方面借签了社桑和达达,另一方面还借鉴了构成主义。从这一点讲极少主义与动态艺术的背景是完全一致的,尽管它竭力回避这种心照不宣的共同根源,以至于最终几乎把构成主义的影响完全抹杀了。但不可避免的是我们不得不从这里开始。美国艺术家托尼·史密斯在芝加哥的新包浩斯学校接受了早期培训。创立这所学校的是拉兹罗、摩霍利-纳基,他曾在包浩斯学院授过最重要的预备课程。史密斯离开新包浩斯后直接到弗兰克·劳埃德·莱特手下当了一段时间的助手。建筑影响着他的整个创造生涯,而人们也很有理由将他相对较晚开始创作的雕塑视为某种建筑作品,只不过除掉了顾客的乏味需求和实际功能。史密斯继承和发展了构成主义的原则。他所创作的作品有一种非人格化的气质,使人想起马克斯·比尔的作品。在包浩斯的圈子里还有一种即使不很一致但也十分盛行的说法,即深信构思本身就足以形成作品。所以像摩霍利-纳基曾经通过电话用色谱和图表订制绘画作品一样,托尼·史密斯也完全有理由从金属板加工厂订做他的雕塑作品,只要说明材料和尺寸要求就行了。
然而,与他年轻的美国同行那种严肃气派不同,史密斯的的一些作品中有一种调侃的味道。例如他的一件作品就是将一支压碎了的香烟加以放大并几何化,矗立在奥登伯格居住的地界边缘。
美国极少主义的核心包括四位艺术家--罗泊特·莫里斯、唐纳德·贾德、索尔·莱维持和卡尔·安德烈。在他们之中,莫里斯和贾德最坚定地遵守"客观"的信条。莫里斯写道:
物质在其特殊的自身环境中,其所特定的一种材料,一个形状、尺寸、布置、固定方式,等等,就具有其自身的充分性和精确性。对真实空间中的客观类型的作品的理解并不直接获得排列和规划的信息……空间既不等同于物体,也不是限定物体的界限……唯心主义的思维将形式看得如此重要是因为形式被视为一种证据,证明作品超越其自身而仅仅为显示结构而存在。客观类型艺术则并不局限于这种形式与事物特殊的两重性之中,因为这类艺术的存在没有一个边界约束它的组成部分,而且也部分地因为对于其间关系的感知是不断变化的,由以上分析还应该明白的是,客观类型的作品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建立于一个特殊的、有限的几何形态或一系列特殊的、诱人的材料的基础之上。一团土坯可以认为是立方体,一堆破布也可以认为是不锈钢杆。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莫里斯的作品着意避开一切符号性的作用,另外,他的某件作品尽管可能非常笨重或者体积庞大,但人们不会认为它具有纪念碑的风格,就像形容亨利·摩尔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作的雕塑那样。要把建造纪念碑的任务交给极少派艺术家一定是头脑发昏了,而美国的评论家们把极少派作品热情地与埃及的金字塔或巴比伦的塔庙相提并论也同样是晕头转向了。极少主义所关心的仅仅是每一件作品的美学感知和它们的哲学背景。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莫里斯的雕塑恰恰反映了一种社会现象,因为只有在一个物质过剩的社会中才会宽容这种狭隘艺术的存在。他本人也许正因为是意识到了这一点才会在后来放弃了极少艺术。
尽管居纳德,贾德比莫里斯更加注重形式的排列关系,但他们的观点相当一致。他在1967年的《那鲁建筑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文章,清楚地阐述了极少艺术的价值。
我想让我的作品不要陷入那些不用思议的假想。我可不愿意去思考什么宇宙的秩序,或是什么美国社会的本质,我不想让我的作品成为通常意义上那么泛泛、全面的东西。我对它没有太高的要求。显而易见,作品的意义和结构是不可分的,甚至不能认为是两件东西的结合。就好像一个单词是毫无意义的。
一种形状,一个体积、一种色彩、一个平面就是它本身。它不应该被认为是一个不相干的整体的一部分。形状和材料不应因其周围的东西而变换。一个盒子或是四个盒子排成一排,任何单个的东西或这样一个系列,只是其局部秩序,只是一种排列,几乎谈不上是什么秩序,这种系列是我的,或是某个人的,但显然不属于个么更高的层次,总的来讲它既与秩序无关,也与无序无关。两者都是事实。
索尔·莱维特主要是对简单形式的序列感兴趣。对他来说,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显示了无限变换中的一种可能性,这种无限的变换可以用一种相同的形式来表现:"对于每一件成为真实存在的作品来说,还有许许多多的其它形式没有表现出来。"像莫里斯一样,索尔·莱维特认为形式是无等级的:"既然没有一种形式在本质上优于另一种形式,那么艺术家就可以使用任何一种形式,从言语的表达(写或说)到物理的体现,它们都是平等的"。但莱维特以一种不同的方式遵守这一原则--他认为艺术家必须抓住第一个构思并贯彻始终,不能偏向任何牵着他走的结论,不能有所折衷,同样也不能试图去预测结果:"艺术家不能想象他的艺术,不能感觉他的艺术,直到作品完成……不能把一个好主意搞糟。"
卡尔·安德烈1935年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曲梅格,他是当代极少主义艺术中最声名狼藉的人物,但与他的艺术无关。他那暴风雨般的私生活近来闹得世人皆知,但在此之前他就因一成不变地使用日常的材料,尤其是普通房屋用砖而颇具声名了。他也像索尔·莱维特一样喜欢形式的排列,它们可以被无限地延伸和扩大,对他来说,木块、钢板或砖头仅仅是中性的、完全一样的单元--它们可以用来表现他的想法,即艺术至少在材料方面不应具有一种特权和身份。他的雕塑是一些物理的存在、但大街上的一堆建筑材料也同样如此(安德烈曾经拍过一系列专门的照片说明这点)。而具有特殊地位的东西,在安德烈来看,是艺术家的构思,是用来表达他的模式的思维方式,就像一盘国际象棋棋子的运动表现的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变化。
前面已经简单介绍了极少派艺术核心成员的作品,在他们的周围还有其他一些艺术家。其中一些人与极少派艺术的关系相当脆弱。例如,加拿大出生的雕塑家罗纳德·布拉顿创作的那些粗大的简单开关清楚地表现出他与托尼·史密斯的艺术有关,但他的作品,如《瑞考一号》和《卡姆·苏特拉》,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更为传统的风格。
理查德·塞拉比布拉顿年轻许多,一直被称为是第二代极少派艺术家。他用金属板或圆木制成的大型雕塑无论从结构上还是视觉上看都属于最简式抽象派艺术--作品各个部分都是靠其自身重量维持着平衡。也就是说它们往往看上去极不稳定,因此令人恐惧--一触即溃而殃及观众。因此塞拉希望他的作品展示于公共场所,这样就可以接触到毫无思想准备的观众。但他与布拉顿不同,对观众有一种非传统的敌视态度,而观众也往往以牙还牙。每当他的野心得以实现的时候,经常会受到激烈的抨击。
极少艺术也曾几度玩弄技术,尽管这不并像对动态艺术那样至关重要。它与技术的关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已有的技术产品作为艺术的原材料;另一种是利用新技术工艺赋予作品与众不同的外表。或许前种形式最著名的代表要属制作霓虹灯管雕塑作品的丹·弗莱文。弗莱文使用标准灯管,有时是白颜色的,例如在《塔特林纪念碑》中;有时是彩色的,如《无题(献给芭芭拉·利普)》,以此模仿最简式抽象派风格。弗莱文的作品与马塞尔·杜桑的现成艺术品有着很强的联系--正如彼得·施尔达尔在他为萨奇收藏目录第一卷所写的介绍中指出的那样:"弗莱文的艺术是一朵温室之花,其基本意义可怜地依附于一种惯例的场所--在这里其非艺术的本质就可以具有尖刻和刺激,作为对习俗的无声的攻击,例如习俗认为是天花板上的灯照亮了墙壁上的作品,而不是相反。"雕塑家拉里·贝尔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他制作的极少派的立方块和大型L形精美雕塑,使用的是最早从航空工业发展而来的涂层玻璃。这些作品是对一种优美材料的性质的展现,其本身就说明了一切。贝尔与弗莱文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是他们作品中那种自相矛盾的豪华和装饰性。
另一位采用简单方块形式的艺术家是简基·温莎,她1941年出生在加拿大。她与第一代极少派雕塑家的主要区别在于材料的选择以及处理材料的方式--她倾向于使用保留有粗糙表面的东西:麻线、胶合板、水泥岩片和钉子。她的雕塑具有一定故意的"手工"的外观,这与极少派创始人们的作品截然不同,而且她经常将她作品单一的块体性打破,比如在立方体上打上孔洞,这样这些作品就可以两种方式理解--或者是封闭的空间,或者是占据空间的物体。美国著名评论家希尔顿·克拉默基本上是敌视极少艺术的,但他把他吝啬的赞扬给了温莎小姐的雕塑。1979年他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评论她的长篇大论,结束时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在她的作品中有一种渴望,渴望一种原始文化雕塑中想当然的意义:一种从传统赋予的仪式功能发展而来的意义。正是这种渴望才是简基·温莎雕塑的意义所在--渴望努力将极少主义那些圆滑的形式反归原始感觉的语言。其艺术的深刻之处在于以下事实:在这项工作中只有当仪式可以表现于雕塑时,才成为具有审美价值的仪式。
埃娃·海丝是美国年青一代极少艺术家中与众不同的妇女,她的生命很短暂。她的作品很少使用坚硬的、几何的、统一的材料。即使在少数情况下使用了这些形式,其表面也被纹理化,或以某种方式掩盖起来。她的艺术从根本上讲是一个过程的记录而不是一种结果,是探索她自己主观的一种方式。她在笔记中写到:"我愿意我的作品是非作品,也就是说它在我的预想之外去走它自己的路。"在一次采访中她说过:
我认为艺术是一种全面的东西,一个人全部的奉献,是一个根本,一个灵魂……在我的灵魂深处艺术和生命是不可分离的,要把一个很直感的念头隔离开来,而去营造某些计算好了的体系并盲目进行下去--常常被认为是很明智的方法--这简直是太荒唐了,应该让灵魂或感觉或是你随便怎么称呼的东西去选择……我喜欢去解决艺术中的一个未知数,而不是生活中的未知数……实际上我现在的想法是将我曾经学过或被传授的所有那些东西反其道而行之--去发现确实属于我的生命、我的感觉、我的思想的东西。
其结果则是只能听其自然了--作品没有明显存在之理由,至少对外部世界来讲是这样。作品的成功只有取决于观众体验到他或她与艺术家达到了某种神秘的和谐--事实上,只有取决于海丝成功地引起某种心灵的回昔。
海丝雕塑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它联系着一些当代著名织物艺术家的作品,尤其是像雷奥诺·托尼、克莱尔·切思勒和弗朗索丝·格洛森。这些艺术家大胆地进行了立体纺织的实验。海丝的作品是由混合材料制成的,如在绳子、电线和线绳之外涂上乳胶,尽管这与同一时间克莱尔·切思勒所制作的物品有所不同,但她们大体上属于同一类别之中,当然切思勒也确实是因其对纺织技术的深厚知识而在处理材料时更胜一筹。实际上,极少艺术强调艺术的"客观性",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美术与工艺之间的传统界限,特别是在美国,自从抽象表现主义之后工艺就越来越走向美术而远离生产,从其本质来讲,绝大多数工艺作品正是极少艺术所追求的--没有象征意义,仅仅是一个物体世界中的又一些物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