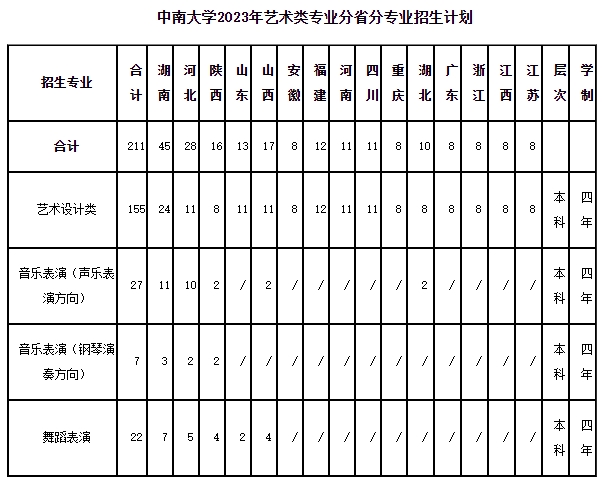风雪夜归人(风雪夜归人的上一句是什么)
我们只需把目光投向“科学史”这段时空,便会发现:所谓的《广告学》,其实连婴儿都算不上,充其量只是胚胎。
拙文“走近奥美”的结尾,我不知天高地厚地预测:超越,需要一个诞生广告灵魂的时代,并且只能从“追问”开始。其实“追问”只是我的直觉,但究竟何为追问如何追问,我几乎一无所知。
作为一个挣扎于现实生存和创作快乐之间的广告人,我经常不知不觉地、独自在历史和常识的分界线上徘徊。当我向历史纵深走去的时候,个体生命的短暂置身人类历史,瞬间没顶。这时候我极度自卑,最明显的自卑感就是觉得自己所有的文字都是不见泰山自以为是,要不就是人云亦云东拼西凑。但是当我走投无路、向常识的方向突围的时候,而且只是向常识靠拢了一点点,我的自卑的一部分似乎被隐隐约约的幽默所取代。这种抽象的、不可名状的变化,发生在我的意识之中。举个直观的例子:我们能够想象么,如果是在十九世纪,我们有勇气怀疑被西方心理学界尊为现代心理学之父的弗洛依德么?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识破弗氏的许多真知灼见只是被书面化的“常识”么?但是不可否认的,在现代心理学后续的发展中,我们发现弗洛依德躲在科学殿堂雕刻得美仑美奂的石柱后面,和我们开了些严肃的玩笑,他的某些惊人的理论和发现里面,有不少是显而易见的“常识”。虽然这丝毫无损于他的贡献和地位,但我们对于这类“常识”的发现回归,也不失为一种贡献。
所以我们既没有必要在当今社会愤世嫉俗,瞧不起每一个我们看着不顺眼的广告大师,也没有必要被大师的光环刺得睁不开眼。合情合理的态度好象是:有什么发现就说出来,“发现”本身就有可能是一种贡献,“说出来”就更加是了。既然一百个人的眼里会有一百个不同的哈姆莱特,那么,我的广告同行们,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慷慨”和“大无畏”一些呢?
我曾在自说自话的“追问”中,发现一些广告的“常识”和这些常识的“线索”。
例如在对广告学的追问中,发现了心理学的线索,沿着心理学的线索追本溯源,又看见哲学的轮廓。
在广告学里找心理学的影子,比在希腊字母里找英文字容易得多。我们现在对于西方广告理论的认知程度,部分取决于我们的知识和经验。在属于我个人的创作资源当中,知识部分显然弱于经验部分,因此我无法在知识的层面获得科学精当的发言权,而中国知识渊博的学者们或者精力充沛的年轻广告人,可以琢磨一下广告学和心理学之间的传承和对应。说不定若干年后有人发现:广告学中的某些理论支柱,
象广告心理学、消费者心理学等等,只不过是现代心理学中较为通行的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变种延伸和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国际市场争夺中的应用。而那些这样那样的“独特”的销售主张,是那时人们认知结构中的“常识”而已。例如认知心理学就特别关心注意力和感觉力的程序,有关语言、思维、解决问题的程序,有关记忆、想象、创作、意识形态的程序等,并且除了研究人的认识过程,即认知的因素,还对非认知因素,诸如情绪、意志、态度等同样加以研究考察。谁能说广告研究就没有经过这条路径?
二百年前有心理学么?没有。一百年前心理学也只不过是哲学中的一个科目。二百年前有广告学么?没有。一百年前广告学还只有一点点苗头。半个多世纪以前,美国的心理学界视欧洲心理学界为权威,直到二战以后美国学术界的独立,才使得美国的心理学界挺直了腰杆儿。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的广告学界也走过类似于心理学界的道路,只不过广告业赤裸裸的“现实性”局限了它发展的脚步,特别是研究领域里的科学试验。这一点似乎在中国的广告界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的广告人在中国七十年代末商业和传播突然苏醒的早晨,来不及穿好理论的外衣就匆匆出街,
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中国的广告界一时之间豪强四起,数数现在中国的广告公司的数量就知道我有没有说瞎话。直到先行一步的港台广告人浓妆艳抹地来了,大陆广告人才见识什么叫口红、什么叫眼霜、什么叫粉饼。
都以为是中国广告的春天来了呢,于是各庄的地道都有了各庄的高招,于是“创意导向”和“业务导向”一个不服一个,于是一个个还没顾上找北,就一骨脑儿投奔了西方。
但一个令他们更震惊的局面出现了:在各自为阵各显神通之际,突然发现,西方的广告资本、结构、理论,正鹅毛大雪一样地向中国大地铺天盖地。而此刻,中国的百姓正在梦乡里沉睡,他们只会在第二天梦醒时分、打开消费之门的时候,才会吃惊:整个世界怎么一夜之间白雪皑皑了。
于是,广告的后来者,那些勤勉的风雪夜归人更加痛苦不堪。他们置行为主义和认知心理于不顾,挥舞着着人文主义的旗帜,奔走呼号、相互转告。但个体生命与社会潮流较量,永远不是“主场”,而且注定输得很惨。但他们满不在乎,寒风中的冰雪在他们满腔的热情之上融化,顺着他们的头发、顺着他们的面颊,滴滴嗒嗒、滴滴嗒嗒,仿佛在唱: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么?
莫非他们,正预示着那个出现广告灵魂的时代的必然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