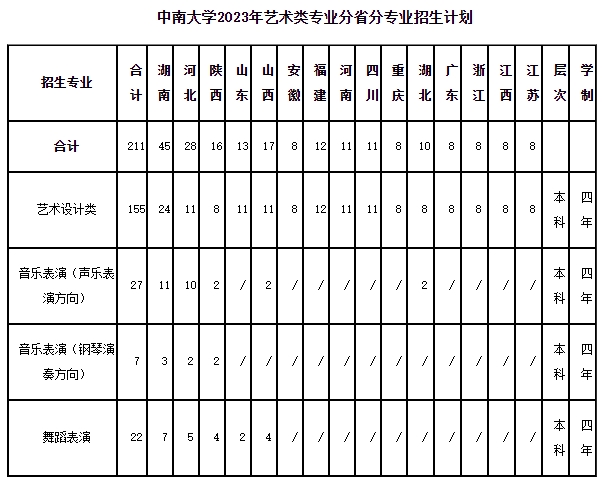老北京装裱手艺
装裱艺术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的民族特色,书画墨妙必须经过装裱才便于收藏、流传和欣赏,因而装裱技术的高低,绫绢色彩的选择与装裱形式的设计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效果;历代书画珍品,如已糟朽破碎,一经精心装裱,则犹如枯木逢春,一些珍贵画文物因此不致湮没失传。
揭裱字画也称装裱字画,古老的名称叫裱褙。北京揭裱字画行业,都自称是“苏裱”。传说是从苏州传来的手艺。明代有位汤勤,乾隆时有位徐名扬,他们是从苏州来京城的揭裱字画的艺师,闻名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甚至皇帝。他们揭裱字画技艺高超,世代相传,精益求精。到了光绪年间,苏裱字画手艺之精巧,出神入化,旧字画碎破到不可分辨,甚至糟脆到呼吸即能吹散的程度,仍可苏裱如原状,可谓是业界一大绝技。一般来说装裱新画容易,但揭裱古旧书画则是要很高技术的。民国年间,北京装裱业大多在东裱褙胡同和琉璃厂一带。前者以糊顶棚、售南纸、做烧活居多,而琉璃厂的装裱铺才是真正的书画装裱行,其主要有刘林修的竹林斋、崔竹亭的竹实斋、马霁川的玉池山房、张成荣的宝华斋……
现代的著名书画鉴定家王禹平学徒于玉池山房,裱画大师刘金涛学徒于宝华斋,裱画名家崔竹亭学徒于竹林斋……可见是名师出高徒了。琉璃厂有20多家裱画铺,光绪末年时,竹林斋、竹实斋最出名,民国初年以来,玉池山房最著名。刘林修和崔竹亭合伙开竹林斋裱画铺,分手后,崔竹亭经营竹实斋,刘林修独自开办竹林斋。他们的手艺都好。经营字画古玩铺的掌柜们,给他们二人起个绰号:“刘二寡妇”、“崔三娘儿们”。
为什么两位男子汉有这样的外号呢?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干活心细手巧像妇女,另一方面是他们的音容笑貌像女人。刘林修见人没笑容,脸总是阴沉着;崔竹亭说话慢言细语,嗓音似女人。他们揭裱字画有绝活,油渍碎裂的旧字画,经他们的手,恢复原样;填补残缺,看不出破绽。马霁川在光绪三十二年先在竹林斋学裱画,后在竹实斋跟崔竹亭学手艺。他把刘林修和崔竹亭的手艺、绝技学到手,1920年在南新华街长春会馆内开设玉池山房。玉池山房装裱名人字画,也经营字画。马霁川的手艺精妙,玉池山房装裱字画很讲究质量,达不到质量要求,不交货,赢得了信誉。当时的北京政府及以后南京政府的要员、书画家、收藏家林森、于右任、张学良、张伯驹、张大千、溥心畲、徐悲鸿、齐白石等,都知道马霁川的名字。马霁川给他们装裱字画,也做他们的字画生意。张学良一幅珍贵的手卷画,日久受潮,画面反铅,白脸人变成黑脸,经玉池山房整修、装裱,恢复原样;于右任收藏的宋元画,年久碎裂,也请马霁川加工修复。老北京装裱的手艺是师傅传徒弟,学徒要先拜祖师爷,谁是祖师爷说法不一,有造纸的蔡伦,有造字的仓颉,有画圣吴道子,也有大儒孔夫子。学徒期间要练毛笔字,学打算盘、练记账、学画格式、形制,熟悉绫绢……
书画装裱十分注重内在质量,这就要求书画装裱师有全面的修养和深厚的功力,这样才能使书画家的作品更好地得以完售,从而提高艺术魅力和观赏力,在长期的合作中许多收藏家、画家、书法家都和装裱师结成了很好的朋友,如:张伯驹与王华轩,吴作人与刘金涛……
新中国成立后,装裱不仅继承了历史上好的形式、风格和技法,而且在整修揭裱古代残破作品方面开创了新的途径,为保留我国古代文化遗产做出了显著的贡献。诸如将巨幅大画《江山如此多娇》以及长达十余丈的《首都之春》手卷等,装裱得庄重大方,平正堂皇,堪称装裱史上别开生面的创举。俗话说“乱世黄金,盛世书画”,如今在书画热、收藏热的推动下,装裱业也快速发展,很多画室、画店使用了装裱机,15分钟即可裱一张画,但装裱机只能干“粗活儿”,要求较高、难度较大的画,还是要靠手工装裱。作为一门手艺,随着一批老艺人的去世,装裱业出现了人才断档,很多画店苦于找不到合适的手艺人,而不敢把名画拿去装裱,那种枯木逢春、出神入化的装裱故事,只能留在传说中了。